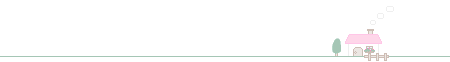
教师爱乐感言
歌缘---一个音乐老师的故事
李兴无
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,家中没有人懂音乐。小时听听爸爸吹口琴,这是我得到有关音乐的启蒙教育。记得我曾想学拉小提琴,妈妈没有答应,那时候一把琴的价钱等于大人一个月的工资呢。我用五毛零花钱买了把笛子,开始自学音乐。在学校里,我参加了合唱队,还参加过区少年宫的活动。记得那时候唱过一首歌叫《长大要把农民当》,没想到以后真的当了农民。69年我随下乡大潮到了安徽,当上了一天只挣两毛钱的真正的农民。插队的生活是枯燥的,劳累之余、饥饿之时只能用吼歌来解脱。我唱得最多的时候是蒸馍的时候,我光着膀子,映着炉火,和着风箱刮哒声唱啊,唱啊。什么苦和累都随之飘去。乡亲们听了,会大声地问:“老李,又在学驴叫唤呐?”在农田里,我也学会了劳动号子。我的嗓门使我赢得领唱机会。我唱:同志们哪!(嘿哟!嘿哟!)加把劲哪!(嘿哟!嘿哟!)我的吹笛,也给乡亲们带来了误会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一天晚上我上了村边的塔顶,天黑什么也看不见,我骑在栏杆上,掏出怀里的笛子,胡乱吹了两段。这一吹可不得了,笛声引来了狗叫,狗叫引出人声,手电的光柱也冲这边来了。我看事情不妙,就赶快回家。第二天中午,村里到处传说昨晚神仙下到塔顶啦,还呜啦呜啦地唱小曲呢。村里的老太都结伴去塔下烧香磕头哪。我听了捂着嘴偷乐。在下乡的四年半中,我还接触了豫剧和当地的民歌民谣。73年,我被推荐上学,由于没有关系,我的名额从上海科技大学被换到亳县师范,但为摆脱农民身份我进了师范。曹操的老家亳县是个文化古城,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。我满怀喜悦,伸开满是老茧的手,学拉手风琴。儿时的梦想吸引着我,劳动锻炼的意志帮助了我,我用每天六小时的练习,很快掌握了手风琴的演奏。
使我改变志向,走上音乐之路的导师,是广东籍的音乐教师邝老师。我参加了学校合唱队,邝老师一下子从队伍中发现了我,叫我担任独唱。我唱得第一首歌是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,那是一首抒情的电影歌曲,由李双江首唱。记得那次在学校礼堂的演出,我十分紧张,前台都报过幕了,我却迟迟迈不开步,邝老师急了一脚把我踹了出去。有了这一次的成功,我终于踏上了歌坛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想起这一幕,我要衷心感谢邝老师,是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。
在小城里,我们这支由广东老师带队,以上海学生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得发紫。我们三天两头被拖拉机接走,去农场,去机关演出。我在演出中也逐渐克服了腼腆,歌唱后的掌声也多了起来。75年我留校未成,只能社来社去,回原插队的公社中学当音乐教师。我是在路线教育高潮中进学校的。我当了文艺班的班主任,带了一班学生天天排练演出。为了报答原插队村的乡亲,我带队回家演出,那次情景,历历在目。舞台搭在高高的土堆上,气灯吱吱地烧着,锣鼓声中我拉琴指挥乐队奏起来。先唱一段小戏。还有表演唱,舞蹈,器乐等。最后当然少不了我的独唱-乡亲们叫它“驴叫唤”的玩意儿。演出结束,老乡都夸:老李这两年学得不错,没想到驴叫唤还真叫出了名堂。中学的隔壁是剧院,镇剧团经常演《朝阳沟》,他们请我去伴奏。我用键盘吃力跟着那些不熟悉的跺板飞板,学到了不少戏剧知识。我的小创作也被剧团用做幕间曲。那时的演出没有报酬,但是,演出后的那顿白菜煮大肉太令人兴奋,这可是真正的“共产主义”呀。在农村中学的八年中,我结识了许多歌友,学生不多说了。有一个右派分子,会唱三十年代的歌,他挑水为生,经常到我这儿唱。后来他平反了,去当党校副校长。还有个剧院看门的小伙,会画画吹笛子,他常来我家,他吹《牧民新歌》我伴奏。后来他被县文化馆录用,他的驴画成了一绝。我的唱歌没有大作为,我的《牡丹之歌》成了哄孩子入睡的催眠曲。有一次,电话通知我到县里去,我因为孩子的原因回绝了,后来知道那是灌唱片的事,后悔也晚了。83年,我调到县师范,在那里,我的才能得到重视。县工会把乐队办到我的学校,电子琴,电吉他就放在我的家。我组织乐队之余也少不了独唱。县里有三个男高音,演出时哪个比啊,
比谁唱得高,比谁唱得新,比谁唱得更有味。演出锻炼了人,使我积累了不少曲目。我的学生也暂露头角,我作曲由学生董小绢演唱的歌曲,被直接送到省里。学生高杰后来接了我在师范的班。86年我离安徽时,全县的音乐爱好者团聚一堂,以歌告别,那个情景,那个规模,令我永远难忘。我为他们最后一次伴奏,他们为我最后一次喝彩。如今你们在哪里,如今你们还在歌唱吗?
96年,我用了八毛钱的邮票联系,调回上海郊区。故乡,你的儿子回来了,去时青春年少,回来一家数口。我们带着农民习惯,他乡的口音,北方的小曲回来了。县艺术节开幕了,我该露一手了。我抱着手风琴硬挤上台,用我的歌赢得评委和观众的赞赏。为教育局夺来了意外的一等奖。我直接加入了音乐组织圈。从此县的大小会议演出有我,慰问解放军有我,大奖赛评委有我。我参加了有关音乐的所有活动。举个例吧,县大合唱比赛时,一半以上的歌队有我参与,那要唱,要奏,要指挥的歌在我脑子里直串调。一场比赛下来我累垮了。
我们有支男声小组唱的队伍,以中年人为主,唱《挑河泥》之类四声部歌曲。刚成立的时候遭到文化馆的领导反对,她批评我们:自由散漫,各唱各调。对这种不懂业务的领导,我们只好一笑了之。男声小组唱很快走红了,它以阳刚之气,劳动气息见长,从基层唱到县城,从县城唱到市电视台,许德明书记夸我们是县文艺阵线上的拳头产品。我也荣获优秀表导演奖。
我最早“触电”是在87年,那次我参加第四届卡西欧大奖赛。选拔赛,评委只让唱了四句,过初赛到复赛,我碰上了周冰倩,周冰倩那时刚出道,音乐学院的学生模样,唱歌还要爸爸陪着。她唱完我上台时,主持人正采访她,我站在满是灯泡的舞台正中等着,手抖出汗,心里七十八下的,很不是滋味了。我参赛的曲目是《船工号子》,歌大特别累人。经过努力,我终于唱完,满头大汗地回到台边,主持曹可凡悄悄地劝我“不错,分挺高的”。我紧张的没敢抬头。
过几天,电视播放时,我才发现我得了8.98分,高出周冰倩0.02分。我第一次尝到“触电”的甜头。(周冰倩后来得了冠军,我获第八,奖了一架电子琴。)
让我转变命运的唱歌比赛,是94年的教师艺术节大赛。那天气温37度,区工会主席带我和前妻来到会场,那是个大学的旧礼堂,为了创造大赛气氛,礼堂里坐的都是组委会请来的学生。工会主席去抽了签。哇,30号,最后一号,我得耐心地等着。在走廊里,我吃着冰棍背着词,吃到第五根的时候,我叫到“来根盐水的”。上师大的老师们也到走廊来亮声,我和他们打过招呼后,心想,坏了,学生怎能和老师比呢!(我那时正在上师大进修),他们来了,还有我的戏吗?终于,等到我上台了,台下学生们累了,台边评委也累了,我很放松地走上台,用尽最后的力气唱道:“说句心里话,我也想家...”唱着唱着,台下活了,有动静了,我更买力了,当我最后的一个高音唱完,台下掌声响了起来。我想,我的任务完成了,学生的任务也完成了。我走下台,无力地瘫坐下来,工会主席问:“能拿奖吗?”我伸出手说:“冰棍。”奖项公布了,三等奖没有我,二等奖有上师大的老师,我想完了,今天白忙活了,什么?一等奖是我,不可思议,一等奖竟是我。两个女人叫起来,跳起来。工会主席指着我“哇!你早不说。装蒜呐!”
要问时来转运是什么感觉,我的感觉也算是一个极端,当时没有兴奋,没有激动,更没有眼泪。我麻木了,我要回家休息,我等了太久了,我的梦实现了。领了奖,主席破例到外面去叫车,她们在出租车上大声地讲,和司机讲那事,一直讲到下车。要发奖了,定在教师节十年庆电视大会上。电视台导演打电话给我,问我有什么想法,我搪塞说我要以此为动力,导演打断我的话说,你有什么困难?我吱吱呜呜说不清楚。后来导演知道我一直想要架钢琴,就大笑起来,莫名其妙地挂了电话。94年9月9日,我着一身米色西装,到电视台报到,参加庆祝大会直播。聚光灯下,任艳问:听说你吹拉弹唱样样会,为什么不下海挣钱呢?我说:我那里的学生离不开我,我要尽我所能使他们能得到好的教育。任艳问:听说你的现在还买不成钢琴,那教学就会不方便。我说:以后会有的。任艳说:那我们就请李老师用歌声为大家《说句心里话》。我的这次的唱更从容了,因为电视台为了质量,已经先期录音,我只要对口型.一曲终了掌声未停,主持把我留住,谢丽
娟副市长上来了。她对大家宣布:李老师是几万人参与的艺术节一等奖,我想以我们教育基金会的名义,奖励他一台钢琴,鼓励他和所以在第一线的教师,希望他们做出更大成绩。摄象机推向我,我又是一阵眩晕,一片空白。当天,上海几家报纸也刊登此事,题为《李老师圆了钢琴梦》。几天后,授琴仪式在教育会堂隆重举行,教育局长代表谢市长授我一台刻有铭牌的《斯特劳斯》钢琴。并敦促区政府落实我的住房。卡车在大道上行驶,我扶着琴站在车上迎风展望,啊,路两旁的鲜花仿佛是为我开放,高架道就象上海母亲的手臂,把我紧紧怀抱。一年后, 我住进了新房,晋升高级,记了大功,加入民进。我进来了人生的最高点。
98年我参加了“马拉松”式的五星奖擂台赛。“马拉松”练的是持久战,我打了八次擂,一共到电视台25次。(一场比赛,送乐谱,合乐,录播共三次。)第一擂把对手拉下台,用的还是《船工号子》。有一场比赛,我发现我的师大老师当评委,心中窃喜,但结果是比分打平,我给老师打电话,他说:“我把评判的权力交给下任评委,我不想别人说我偏心。”我在下一场,以拿手的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取胜。遇一女歌手,唱得棒极了,但她的《长江之歌》第一句加了附点。比赛就是比谁发挥出色,谁少犯错误。一次我冒险唱《再见了,大别山》,我又“违
纪”在间奏中加了我的“广告”:献给插队的田营村的乡亲们,结果评委被我深情感动,不记小节,让我过关。我一次又一次上“断头台”。一次又一次用练气功放松自己,一次又一次利用了对手的紧张,我的奖金数在上涨,我的歌也“弹尽粮绝”。第八次我唱《祝酒歌》,对方以《回四川》应答,双方棋逢对手,旗鼓相当。就看评委了:亮分93:92,我明白,该“光荣退休”了。后来一打听,《回四川》是评委的学生。(哼,他的老师比不上我的老师。)总结擂台赛,我最大的收获是,好象开了八周的独唱音乐会。
天有阴晴圆缺,人有喜怒哀乐。人生就象一台戏,唱过喜歌也该唱悲歌。我的新歌是“一瓠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。”那是在李叔同的墓前唱的。她走了,争吵到起诉只用三个月。25年的情感毁一旦,弘一法师,你能告诉我怎样去看破红尘?西湖畔歌如潮人如海,又谁能抚平我滴血的心... 我去唱圣歌,我去学阿炳,我最后考上了曹丁指挥的平安合唱团。合唱团具有专业水准,由转业歌剧院演员和音乐教师及音乐学院学生组成,著名指挥家曹丁精心辅导,使它胜任中外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演出。合唱团经常与外国同行交流,同台演唱,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团里要排[田丰]的作品,要选领唱,我自告奋勇,以我的实力得到这个位置。这是一部描写哀牢山人民插秧对歌的无伴奏合唱,领唱旋律舒展嘹亮,伴唱节奏鲜明,我们的演出在音乐厅,不用话筒。演出那天,盛况空前。领导来了,交响乐团来了,刘秉义来了,我的名字也打入了音乐会说明书。哇!人生能有几回搏,我拼了,演唱时我的声音一出,把指挥吓一跳,他冲我直挤眼,嗷,我太激动了。在有名的“水晶宫”大剧院的演出,我唱的是吕其明的《弹起我的土琵琶》。从台上望去,剧院层层大红的座椅,无数的观众为我们鼓掌,台前鲜花盛开,台上乐队轰鸣,我想起了在土屋风箱伴奏下的吼唱,我陶醉了,我满足了,我的今天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,当我老了时候,我会指着大剧院对下辈说,我在那里领唱过。
![]()